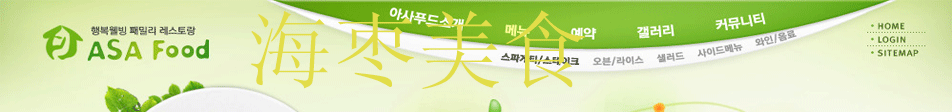|
年冬天,老贺(本名贺中)去探望“退隐”诗人马高明,还在他家中翻到了年版的《北京青年现代诗十六家》。看到这本有着特别意义的“北京诗集”,老贺的思绪被拉回到了上世纪80年代,那个中国当代诗歌蓬勃发展的“黄金时期”。 诗人老贺。/受访者供图 在接受《新周刊》采访时,老贺回忆了《诗歌报》年举办的“现代诗群体大展”,那次大展发表了多位中国当代诗人的作品和宣言,对方兴未艾的第三代诗歌进行了一次空前的集结与展示。从那以后,更真实、更生动、更具现代性的诗歌写作,逐渐成为了诗坛的主潮。当然,在这座里程碑上,不乏顾城、食指、芒克、雪迪等一众土生土长的“北京诗人”。 80年代末,老贺在北京开始了诗歌创作。在他的记忆里,虽然诗人在各个地方均有分布,但北京是最具有影响力的中心场域之一,诗歌写作的地域性非常明显。随着时间的推移,城市之间的文化和经济交融成为常态,地域性也渐渐变得模糊起来。 “将三十年放在三个月里浸泡/多余的时间/从院墙上缓缓坠落”(老贺《六月里的无题》)。 老贺的诗里,时间总是“具象”又“虚幻”,正如时间一晃过去了三十几年,当“北京诗人”的概念不自觉地在他脑海中出现的时候,一切都恍若隔世。同时,一个疑问也产生了——作为成长地标与时间流淌的“北京诗歌”线索是不是中断了? 《燃烧时间的灰烬——北京当代诗人十九家》老贺编 带着这个疑问,老贺从以北京为核心的朦胧诗开始往后梳理。他发现,当80年代全国性诗歌运动开始后,更多的年轻诗人进入了新诗探索时期;90年代,全国各地的精英和知识分子云集北京。自此以后,因为当代诗歌的渐渐边缘化,“北京诗歌”无论是从地理上还是从文化上,都先后淡出了大众视野。 然而,不能忽略的是,早年由北京青年诗人成立的“太阳纵队”“白洋淀诗群”“圆明园诗社”等继承下来的诗歌传统,一直在每个“北京诗人”身上自由地延展。 在老贺看来,诗歌创作可以有地理特点,但诗歌不应该有地域之分。如今,仍然用30多年前的方法进行收录,多少是有些对随时光已逝的“北京诗歌江湖”的追慕,但也不失为一种重新开启的角度和方式。毕竟,诗歌才是主角。 朦胧诗之后,谁是“北京诗人”? 年夏天,黑大春与雪迪、大仙、刑天、殷龙龙、戴杰、刘国越等一批北京青年诗人成立了“圆明园诗社”。据他们回忆,那个时候圆明园不收门票,整个区域都是开放的,骑车从一零一中学穿过去,夏天的芦苇跟人一样高。福海有时候有水,有时候没水,阳光照在山坡和芦苇上,仿佛一片野景。 在这里,诗社举办了多场诗歌朗诵会,吸引了北京一批又一批的大学生。继70年代末期的朦胧诗之后,“圆明园诗社”以风格迥异的诗歌创作,对诗界产生着影响。 黑大春、戴杰、刘清正(从左至右)与北大学生在“圆明园诗社”活动中留影。/受访者供图 老贺早在80年代便结识了不少“北京诗人”,正是这些诗人和诗,对老贺产生了不限于文字和审美上的影响。读黑大春的诗的时候,他的视觉与听觉生动转换,体验与想象力高度融合,现代汉语抒情诗居然可以这么美妙——“仿佛最后一次聆听漫山遍野的金菊的号声了”(黑大春《秋日咏叹》)。 —年间,老贺在选编诗集时,注意到了许多曾经被朦胧诗的光芒掩盖的“北京诗人”。他试图串联起这些“散落的珠子”,便确定了三个标准:一是朦胧诗之后的诗人,二是从小在北京成长起来的诗人,三是基本已进入创作成熟时期并且一直坚持在写诗的诗人。 在这个过程中,老贺发现了不少“遗珠”。 “比如宋逖(本名王京生),我对他的诗印象深刻,但以前不知道他是北京人,虽然我们认识。”老贺把诗歌和北京联系起来后,身边的“北京诗人”便一一浮现出来。《北京诗刊》的主编李津兰(诗人守静笃)经常让老贺给诗刊推荐诗歌作品,但其实她自己也一直在创作。作为好友,这样的“打探”也让老贺对他们多了一层了解,随着“收集”越来越多,那些自然地浸染过北京气息的诗歌,也都变得清晰起来。 近期,老贺编写完《燃烧时间的灰烬——北京当代诗人十九家》一书。/受访者供图 最让老贺意外的是黄燎原,在他印象里,黄燎原一直在写作、音乐节、画廊之间切换。平时不怎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