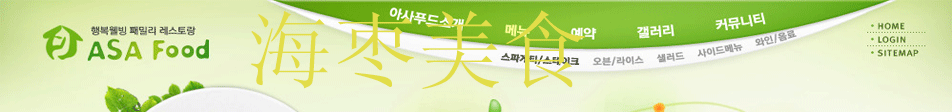|
年12月3日,应北大“九十年代”社团的邀请,一众圆明园画家在北大三角地旁举行了北京大学九十年代现代艺术大展。展览引起了很大的反响,随意放置的画作以先锋的画面语言挑拨着过路人的神经,一种久违的兴奋在九十年代初沉闷的北大校园里蔓延开来。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 年,方力钧从中央美术学院毕业。当时中国劳动力就业结构多元化的改革初见成效,工作分配的制度渐渐退出历史舞台。26岁的方力钧没有接受学院的工作分配,而是住进了挂甲屯一户农民的小院里。在那里,方力钧陷入了对绘画的狂热之中。 八十年代热烈的文化格局被荡平,“空白感”充斥在人们的内心。方力钧认为这恰恰是一个历史契机,一个空荡荡的文化舞台正等待着才华横溢的艺术家们去填补空白。 上学时代因为头发长度不合格而索性剃光头的经历让方力钧体会到了“叛逆的成功”,也为他后来的艺术创作埋下了伏笔。方力钧创作的光头形象“一下抓住了读者的神经”。“被剃头之后,每个人都很差不多”,这是方力钧成长年代的寓言,通过打碎又重建,方力钧赋予了光头个性与真实的意味。这些画作,与当时王朔的小说、崔健的摇滚共同构成文艺在90年代向揭示个人真实情境的转变。 带着极为强烈的个人风格的创作让方力钧获得了艺术上的成功。评论家认为,作品中所呈现的无聊情绪和“一点正经都没有”的“泼皮幽默”敏感地把握了当时中国人普遍的存在方式,被誉为“中国当代艺术教父”的栗宪庭将这种艺术风格命名为“玩世现实主义”。 方力钧变成圆明园画家村的先导者和“金字招牌”。田彬、丁方、岳敏君等许多艺术家陆续而来,逐渐聚集在福缘门社区。到了年,一批艺术家们开始了他们的“集体聊天”,试图在交流中找出一种艺术上新的表达方式。徐一辉、杨卫是这场聊天中的主导者,他们与其他人每天坐在一起聊,“越聊越高兴,一下聊了两个多月”。这种聊天的结果带给中国现代艺术的影响是巨大的,所谓的“艳俗艺术”就诞生于这样的谈话中。 “我们为什么非要把民间的,像磨漆画、刺绣、陶瓷这些囊括到我们这一类的风格里来?就是要区别于前面类似于波普这些东西。批判的东西更被人看好,不批判的话就面临一个知识分子两难的态度,就是他现在要的是一种发泄,一种不满,而你居然拥抱了这种东西。” 至此,丁方、方力钧、岳敏君、杨少斌、徐一晖等一批当代艺术家,和他们所在的圆明园画家村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进入了人们的视野。 艺术家的“理想国” 与方力钧不同,十九岁的田彬来到北京之前生活在几千公里之外的深圳。当时,经济改革逐渐深入地方,以经济效益作为考核标准的理念渗入各个国有机构和部门,全国各地从上至下的文化机构成了首先被“革除”的对象。大量的文化机构关闭改制,体制内艺术家们的宽松创作环境消失了,刚刚从象牙塔中走出的艺术专业学生更是面临着“毕业即失业”的局面。再加上地方上对于艺术创作的偏见和限制,象征着兼容和开放的北京成为了艺术家们心中的“圣地”。在特区文化建设的过程中失意之后,田彬动了来北京的念头。 年,田彬与方力钧在圆明园福海附近合租了一套农民的房子。这样的农村院落,每月的租金是两百元,对于大部分囊中羞涩的艺术家们来说尚可以承受,而且这里提供了比城市楼房更为宽松的创作空间。周边高校的便利设施也是对艺术家们极大的吸引:福缘门距离北京大学不到两公里,北大食堂的饭菜、大讲堂的电影、开放的课堂和讲座、免费的运动场所,甚至澡堂都是当时画家们生存的倚赖。 “生活很穷,但不是苦”。在圆明园画家村,艺术家过着一种纯粹的、“物质需求降到最低”的生活,热情在冰凉的水泥地上向画布宣泄。这样一种艺术的、自由的生活状态对挣扎在理想与现实裂缝中的艺术家们的诱惑力是绝对的。越来越多的艺术家开始向这片区域聚集,跳出世俗的生活圈,致力于在这片充满艺术氛围的村落开疆拓土、重获新生。圆明园画家村的雏形由此出现。 伊灵原名郭新平,原本是上海一家纺织厂的普通工人。因为不甘心过平淡的人生,他早年曾抱着闯荡的热情独自骑自行车环国旅行。年前后,他骑车路过北京,本只是打算歇会儿脚,没想到随即被北京的人流吸引,成了北京最早的一拨流浪艺术家之一。他年纪并非最大,但是因为“与生俱来的领导才能和非同寻常的凝聚力与感召力”,被朋友们习惯称呼为“老郭”。久而久之,“爱管闲事”的伊灵成了画家村的“村长”。 “当时有个画家叫印俊,他胆囊炎发作了,很厉害,没有钱,就是伊灵提议大家凑一点医药费。当时可能有钱的人都出了些,像方力钧等人,大家给他凑了一两千块钱做手术。还有像后来当地派出所老找他们麻烦,画家面临在这儿能不能生存的问题,他们聚在一块儿开会,好像都是由伊灵挑头儿做的。”画家村的徐志伟回忆。 这样的热心使得初来乍到的画家们对这个社区多了几分认同感与归属感,画家们也因为共同的经历而产生了独特的情谊。杨卫称画家村为“花果山一样的乐园”。多年后艺术家们回忆起画家村的生活,“友爱”仍然是其中频频出现的主题。 “文化舞台”的高潮与落幕 年,圆明园画家村的艺术家们打着“为北大的新文化开路”的口号,在北大办了一场展览。画家村里来自全国各地的“盲流”艺术家们聚集在北大,成为了九十年代“愤懑、张狂和波西米亚式”的校园文化见证人,同时这场展览也是圆明园画家村步入鼎盛期的前兆。 年,画家村已经汇集了将近名艺术家。在福缘门社区这片小小的区域中,几乎每一个院落里都住着一位艺术家。 一批成功者开始引起国际艺术界的
|